奇技淫巧
张岱临高见闻录 | 波尔布特 | 约 2051 字 | 编辑本页
父亲的话,张岱刚听到时松了一口气,以为自己想太多阴谋论了,皇帝死于意外落水着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这很正常。但后来一想到“昏君”的词眼,张岱马上又解读出了另一层意思——你想太多忠君思想了(不要有心理负担),对于宠信阉人和“奸佞”的“昏君”,用制造“意外落水着凉”的方式弑君我们文官集团早就不是第一次干了。
此时,父亲已经咽气了,他再也没机会找父亲问个明白,也没胆量去找钱谦益等其他东林大佬询问这件事。
而他此后则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,远离“功名利禄”——张岱这种远离政治的“逍遥派”生活态度,可以说一半是被东林大佬们的虚伪给恶心出来的,一半是被他们的心狠手辣与神通广大给吓出来的。
收起自己的黑色回忆,张岱与白斯文又聊了会儿,忽然间餐厅内响起了丁当丁当的声音,寻着钟声望去,却是餐厅内的自鸣钟的钟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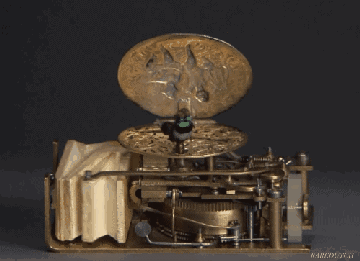
白斯文道:“不知不觉到了澳洲时辰两点了。”
张岱问:“那是?”
白斯文道:“这是自鸣钟,每到一定时辰就会自行打鸣。”接着把自鸣钟的作用对张岱简略说了一下。
张岱听后笑道:“这是女人用的东西。”
白斯文道:“想来男子又是个俗物,不配用了。”
张岱道:“不是这么说,岂不闻‘作奇技淫巧,以悦妇人’(出自《尚书•泰誓下》)?可见得惟有妇人方悦奇技淫巧。这个自鸣钟,不是奇技淫巧么?所以说是女人用的。”
白斯文道:“那么说凡是巧的东西,都是女人用的了。”
张岱道:“这有个分别,巧而有用的,比方这钟本身,何尝不巧,然而钟摆在家里,一家都可以知道时候,这就是巧的有用了。至于这个自鸣的机关……偏不要知道时候,何必要打呢?若说听得远,只怕十丈以外,就听不见了。要知道时候呢,抬头一看,就知道了,何必要听。而且有听着数的工夫早也看完了,何况还有错数的时候呢。”
白斯文又道:“晚上没灯亮的时候听听,不是用处么?”
张岱道:“到了晚上,没有亮的时候,不是睡觉了么?还问时候做甚?”
白斯文呆了一呆,道:“宗子兄所言甚是,我原本也想去澳洲铺子买个自鸣钟,现在看来不必了。”
张岱道:“未必,若只是看时辰,这澳洲自走钟还颇有用处,贤弟不妨买一台放家里,但自鸣机关就有些画蛇添足了。说起这个,愚兄在澳洲船上,也见过类似的奇技淫巧之物。像我房内的电灯,将房间照得同白昼一般,那个做法岂不是极巧?然而又极有用,就不能算淫巧。但我在船头,却看见一个电灯,像一个筒儿似的,就放及灯笼的亮,灯前还置木板机关,让灯一闪一闪(张岱看不懂灯光信号与莫尔斯密码),这有甚用处呢?这就是奇技淫巧一类,不过哄着娘儿们玩罢了。”
白斯文站起来说道:“罢了,罢了,时间不早了,小弟还要回去向家父复命,宗子兄不妨跟我去府上做客,明儿我们继续聊!”
张岱也起身道,“那我就叨扰斯文贤弟了,但再去贵府之前,不知斯文贤弟可否带我去临高的书铺一游,临高书铺中可有本地的《缙绅录》卖?吾欲拜访本地贤达,以探查本地民情。”

张岱来临高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澳洲人“吹嘘”的“人间天堂”、“千百年未有的治世”,一路走来他也确实见到了临高市面的繁华,但这一切并没有让张岱产生任何感到惊奇的地方。尤其是在见识过澳洲人如何在广州抓光乞丐和整顿市容之后,东门市的整洁、无乞丐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早在广州润世堂跟刘三谈话的时候,他就断定澳洲人会不惜金钱人力把临高装点一新用以粉饰太平——不外乎当年隋炀帝的故伎——出了临高可就未必如此了。因此,他将这次来临高的考察重点放在了临高以外的海南城乡地区。
而要在脱离澳洲人“关照”的情况下考察海南城乡,不管是找人带路、寻求相对体面的食宿还是确保人身安全,当地缙绅的支持与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同时,张岱也相信,跟“话不投机”的澳洲人相比,他跟本地的缙绅更容易有“共同语言”。最重要的是,万一澳洲人将来真的打到江南甚至夺取天下,在如何向澳洲人“投诚”的问题上,相信自己可以提前从海南当地的缙绅那得到答案。
白斯文想了想,道:“本地的《缙绅录》就不必去书店买了,我家就有。”
一小时后,张岱主仆跟随白斯文来到“白府”——“碧瑰园”住宅区内一座“澳洲式”的花园别墅,北面是一幢两层的“澳洲式”平房,南面的院子里是一片青草地,东西两面有花坛,种着些不知名的花朵、灌木。
进到房中,张岱与白斯文的父亲见面,互相客套了一番。
之后,白斯文带张岱进书房,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琼州府政协委员名录》递给张岱。
“政协委员是澳洲人对缙绅的称呼?”张岱奇道。张岱离开广州时,元老院在广州只有工商联,尚未组织政协,黄秉坤在谈临高情况时,不好意思说家里人早就投髡了,因此也避谈“政协”,因此张岱此时是第一次见到“政协委员”的名称。
“应该是吧!自从我上次出了事,我爹四处托人搭救,虽未成功,却意外得到了这本书,听人说,书上的人都是能跟澳洲官府说上话的琼州府本地缙绅。”白斯文回答道。